1914年6月14日,船山学社在湖南长沙宣告成立。此后举办会讲,出版学报,搜刻船山遗书,开办船山学校,传播船山学术,皆极一时之盛。这个在中外有一定影响的船山学社的创办人,就是至今尚不完全被人认识和了解的刘人熙。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同治六年(1867)湖南乡试第一名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屯田司行走,派则例馆纂修,改总校官,加四品衔。光绪十五年(1889),以直隶知州外放河南补用,先后委署许、光直隶知州,加盐运使衔。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以道员改官广西。次年(1901) ,清政府颁发“预约变法”的“上谕”,进行所谓“改革”,刘人熙应江西巡抚李兴锐之聘,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课吏馆副馆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柯逢时任广西巡抚,奏调刘人熙入桂,任课吏馆馆长,兼营务处会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刘人熙回湘主办中路师范学堂,被推举为湖南教育会长。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0月),湖南立宪派发动兵变,杀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谭延闿被推举为都督,任命刘人熙为民政司长。未几,解职。此后,刘人熙先后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谘议及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政治顾问,往来京、长之间。1916年6月,湖南人民反对袁世凯和驱逐汤芗铭的斗争取得胜利,7月5日,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任命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未到任前由桂系军阀陆荣延暂行兼任。但湖南军政各界坚决反对,临时推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兼省长。8月4日,北京政府改命谭延闿继任。1918年4月,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了湖南,倒行逆施,穷凶极恶。这时七十五岁的刘人熙危不自保,便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潜往上海。并担任了策进永久和平会会长,与孙中山相往来。1919年4月,病逝子上海。时值南北对峙,北京政府、广州军政府均发电悼唁,并遣派专使,拨付专款,赶赴上海致祭,各省亦纷纷派员祭奠。
刘人熙虽从政数十年,但不放松学问,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从二十六岁开始,服膺程朱理学。三十五岁读王船山《周易外传》,赞扬船山“学贯天人,独往独来”,于是大力提倡船山学术,创办船山学社,使船山的思想得以在湖南传播,并在全国产生影响。
二
刘人熙虽然生长在清代末年,走的是同时代一般读书人诵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入仕的道路,但他治学却有自己的特点。他不愿于训诂考证之学下工夫,而对程朱学派的理论很感兴趣。他二十几岁便有志于“道”,躬身实践,未尝稍懈。他后来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说:“辛苦为学四十年,始觉改过迁善,粗有受用。今日差可俯仰泰然,亦数十年责罪忏悔之力,不知几经扎硬寨、打死仗也。”他一生注重区分所谓“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致力“存天理,去人欲”,他推崇船山的为人,主要是推崇船山“彻骨疗沉疴,焉得辞老丑”之类的内省功夫。他从理学的角度接受了船山学术思想中属于“节取程朱”的那一部分。他甚至认为非发扬船山学术思想,不足以正人心,救败乱。他称颂船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把船山著作看成是精神力量的泉源,昭苏万物的雷电,普照大地的日月,超凡入圣的丹药。他在光绪十一年三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读船山书,如观沧海,酌之而不尽也,望之而无涯也。洞心骇目,若雷霆之震于春夏而万类昭苏;切理餍心,若日月之照乎万物而群邪匿影。”又在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熟读船山书,方知圣贤言学言治,真是金丹入口,凡骨皆仙。”他把船山著作中的某些语句作为信条,经常用以鞭策自己。例如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日记:“仔细检点,通身俱是病。船山先生云:‘彻骨疗沉疴,焉得辞老丑。’此真先哲艰苦之言。”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船山云:‘朝市令人昏,入山令人傲。谁知香傲两俱非,但说林泉是高蹈。’鄙人风尘奔走十三年,颇去其傲矣,然得毋流于昏乎?深用自省。”他把第一次读船山著作作为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转折点,把读船山书、学船山为人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他在一首回忆过去学习情况的诗中说:“少年学文史,志必取公卿,冠盖过闾里,出入有光荣。壮岁忧患余,乃知外物轻。途穷思通轨,邻里得友生,赐我一卷书,能令盲者明。”五十岁自我反省时说:“三十志学,百岁为期。五十无闻,秉烛以追。”他在七十四岁时还感慨地说:“可怜一卷船山学,壮岁抄书到白头。”
刘人熙把船山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修身省察的准则,不仅以此要求自己,而且以此衡量别人。凡他所推崇的人,必定是他认为读船山书最用功,学船山品格最有成效,继承船山学术思想最有希望的人。在他的一些朋友中,他最钦佩欧阳中鹄,认为欧对义理之性比自己“见之明,守之定”。他在《和瓣姜读姜斋自定稿》一诗中说:“此嗟志学晚,四十犹区区。假我三十年,十驾誓与俱。瓣姜学姜斋,衡岳起灵符,分我鼎一脔,时时致行厨。”他对于欧阳中鹄是总觉自惭不及的。在他的学生中,他所器重的是王芝祥(字铁珊,系刘人熙之内弟),认为王是““暗室一灯,他日传船山之学者,必是人也”。也对欧阳中鹄和王芝祥作过这样的评价:“近日吾所见欧阳瓣姜、寿椿于王铁珊(芝祥字——引者),皆非一国之士,非曾、左所及。能否见用于世,则不敢知矣。”刘人熙认为欧、王非曾国藩、左宗棠所能及,其根据自然在于欧、王都喜读船山书,学船山为人,乃崇尚“圣学”的立德者,较之曾、左的徒以戎马立功鸣世,而非衷心景慕“圣学”,就高出一筹了。
刘人熙一心希望自己能超凡入圣,也希望别人惟“圣学”是依。在他看来,清季以还,世教衰微,廉耻道丧,政以贿成,人以利聚,“士大夫能跳出势利圈子者,千不得一。”他愤慨地说:“社会之现象,畏难苟女,幸灾乐祸,网利营私,嫉贤妒能,非一翻大震动、大改革,未易见民德之新也。”这个能够新民德的“大震动、大改革”指的是什么呢?刘人熙解释说:“大抵学术明则人才出,人才出则气运回,气运回则天下事方可收拾。”那末,这个能够收拾天下败局的学术又是什么呢?刘人熙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方今朝政昏暗,前途正未可知。亦莫非传播船山学说,为兴起中国之种子。所可为者,如斯而已。”这就是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的思想基础。应该指出:刘人熙推崇船山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从维护已经崩坏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动机出发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发现和赞赏船山学术思想中真正价值的东西。他企图运用船山的存在很大局限性的伦理道德学说作为“大震动、大改革”的理论根据,不仅是行不通的迂腐的空想,而且他夸大意识形态对社会演进的作用,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三
刘人熙是个有心经世的人。他曾说:“志欲仁天下,术难谋一身。”所谓“志欲仁天下”,是说他有政治抱负,希望于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少小孤贫,青年时代生活于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所以他有忧国忧民之心,常思尽力而“仁天下”。他居京十二年,一直在工部供职,既非大僚,又非言官,但他却多次上书言事,希望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有裨于时政。他成进士不久,正值沙俄侵占我国领土伊黎,清廷先后派遣崇厚,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先足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了损害国家权益的《里瓦几亚条约》,继而曾纪泽赴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虽争回了被划失的伊黎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仍划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淖尔以东地区。对此,刘人熙极为不满,他上疏力主对俄用兵,请诛崇厚而严斥曾纪泽。因未被采纳,又联络户、礼、兵、刑各部主事、员外郎及内阁中书等十三人上公疏,力陈和战得失。此后对俄、对法、对德、对日,每开事端,刘人熙都上疏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都披“留中”,从未见有答复。由此,他看清了执政者的腐朽面貌,觉得自己呆在朝廷,“譬之处破舟之中,任舵工篙师之横行,不若登陆而谋补救之术”。于是想离京外放,谋治一州一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后来在许州、光州任知州时,因限于主客观条件,并没有创建显著的政绩。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刘人熙担任了谭延闿郁督府的民政司长,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却为他以后办船山学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他为谭延闿稳定胡南局势出过力,所以谭给了他以办社的方便:(一)拔四千元,作为船山学社的日常用度;(二)拨旧仕学馆(即今湖南省人民医院地址)为社址。刘人熙也以礼相报,请谭任总理,而自己则从事具体的筹备工作。由于作为社址的仕学馆被红十字会及其附设医院占用,一时无法腾出,刘人熙便租用广益学校几间房屋为筹备处。这样,船山学社的组建正式拉开了序幕。但就在这个当儿,“二次革命”发生,未几失败,袁世凯任命亲信汤芗铭督湘,谭延闿出逃,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筹办船山学社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四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发布命令,废除中小学的“读经科”和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但袁世凯任总统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读经尊孔,支持设“孔教会”,出版《孔教会杂志》,为复辟帝制造舆论。刘人熙办船山学社,正是在这样一种气围下进行的。但他办船山学社和那些鼓吹复古主义的人们不一样,并不是为恢复帝制服务,而是真诚地希望发扬船山思想,以匡时救世。他是赞成共和、反对帝制的,曾规劝过袁世凯,斥责过杨度、刘师培等“六君子”,毅然辞去总统府的政治谘议。在袁世凯大演复辟帝制丑剧的时候,他基本上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任命他的爪牙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企图彻底扑灭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汤芗铭一到长沙,首先就捕杀了谭延闿任内的财政司长杨德邻、警察局长文经伟、筹饷局长、会计检查院长易宗羲等十六人。刘人熙因在先一年的九月去职,他认为自己与二次革命无关,所以还安居在他的公馆里,静观形势变化。第二年,他写了一首《竹枝词》:“去年今日忆长沙,袁兵袁将虎张牙,将军晋爵兵双饷,杀尽冤家做帝家。”颇见他当时的心迹。不久,有人劝他暂时回避,他只得回到浏阳。三个月后,刘人熙的内弟王芝祥因与袁世凯的参谋次长陈宦交谊很深,托陈说项,请汤对刘予以照顾。因之,汤芗铭便把刘人熙从浏阳请到长沙,聘为都督府政治顾问,让他出省考察。于是刘人熙以赴东北考察农垦事务为名,率领船山学社筹备处的几个人,于1913年11月离开长沙。刘人熙此行的真正目的在于创设船山学社,所以他一到汉口便停了下来,当天就上书副总统黎元洪:“人熙念民国元气,系在人心;人心不正,皆由国学之不昌。固组织船山学社,阐其大义微言,以津逮邹鲁。”过了几天,黎元洪召见刘人熙,表示支持,并愿为船山学社募捐。接着,刘人熙便和随行人员继续北上。抵达北京后,刘人熙通过陈宦,给袁世凯递上“呈文”:“窃惟民国肇造,非昌明国学,无以发挥固有之文明,消弭潜伏之祸乱。人熙于民国元年承泛民政司长任,即鸠合同人,发起船山学社。思集合俊才,讲求正学,由船山以津邹鲁;发行杂志,以为海内学者之媒介。诚以王先生夫之,在前明遗老中精深博大,独往独来,其魄力实在黄犁洲、顾亭林、李二曲之上,非徒一省一乡之模范,实民国正学之先河。拟建船山祠堂,以隆俎豆,而资观感,为全国之津梁;并次第搜求遗稿,修正发刻遗书,为图书馆之预备;兼渐次设立船山学校,以冀转移学风,造救未来之人才,冀广船山于天下。顾一年以来,地点未定,虽经省议会拨岁费四千元,而开办之费,尚属缺如。拟请大总统提倡,以收风行草偃之效。查大同会已经解散,财政部没收之余款尚有数万金,拟请钧府指拨为船山学社开办经费。大总统日理万机,注重国本。人熙虽衰庸弩劣,亦当竭其一得之愚,助民国维新之化。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刘人熙的这一呈文很快就由袁世凯批交国务院。国务院当即作出如下指示:“先儒王船山,当贞元绝续之交,植内外纲维之辨,播诸来祀,用造新邦,缅溯徽猷,允宜崇报。所称发起船山学社,并拟搜求遗著,建祠设校各节,用意甚善,应即妥慎筹办,俾观厥成。至所请将没收大同会款拨充经费一节,是否可行,并仰径呈财政部核示可也。”
刘人熙见国务院这个“批示”对请求拨款给船山学社一事予以推诿,便立即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请其玉成。但熊回信不同意。对此,刘人熙感到很愤慨,无法中只好去拜访参议院议长李经羲和副议长张国淦,又谒见袁世凯。但因熊希龄反对,致事无成。在此情况下,刘人熙只得恳求陈宦写信关照汤芗铭对船山学社予以扶植。陈宦的信果然起到了作用,汤芗铭表示愿意支持,因此刘人熙在1914年5月离京回湘前写信给陈宦,深致谢忱:“船山学社事,前承致书湘督,昨社员来函云,可以发生效力。玉成高谊,非仅人熙一之人私感也。”
刘人熙回到长沙后,汤芗铭给他解决了船山学社的场地问题。刘在日记中写道:“拨思贤书局为讲舍,有园亭之胜,兼有专门出入,可为船山祠堂。”有了场地,刘人熙就延聘人员,开展了整修房舍、发展会员、搜寻遗书、收集雕版等活动。1914年6月14日 ,船山学社正式成立,公推刘人熙为学社总理。
五
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具有下述特点。
(一)政治倾向的进步性。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其忧中国奈何?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凌,人人有亡国灭种之惧,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家危而不亡。”这几句话,表达了船山学社会员们不满北洋军阀统治,要求改革现状和主张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使民族得到解放的思想与愿望,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十六日,船山学社会讲,听讲者数百人。廖名缙(政学科主讲)讲演,声泪俱下,场内为之抽咽。这是一次对袁世凯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大声讨。为了激发国民爱国思想,《船山学报》每期还辟有《国语》、《邻戒》两个专栏,分别选登国内外大事,特别是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二)学术思想的保守性。刘人熙办船山学社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但他的学术思想却是保守落后的,甚至是复古倒退的。
(1)表现在对待儒学与新思想的问题上。刘人熙维护传统的儒学,反对新思想、新观念。他在阐发会讲要义时说:“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删诗订礼,正乐,赞易,作春秋,大义微言,挹之无尽。我辈幸生其后,时习默识,以日辟其新机,此乃无尽之藏也。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在刘人熙看来,一切学问都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那是个“日辟日新”的宝藏,其他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异端,应当摒弃。廖名缙在讲演中甚至说:“国体改变,是我国无上光荣之事。然弊亦乘之。六籍泥涂,五经刍狗,家习强权之说,人师◇之跖之行。沧海横流,陆沉无日。”这就是说,当前之所以出现社会危机,是因为儒家经典被忽视以至于废弛,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而这一弊窦,又是伴随共和制而产生的。显然,作为立宪派成员的廖名缙,对辛亥革命是不满的。刘人熙和廖名缙在这一点虽然有分歧,但在维护传统儒学、反对新思想方面,他们是无二致的。刘人熙在一次讲演中告诫大家说:“百般科学皆在吾道范围之中,而吾道乃百般科学之渊泉也。”这里说的“吾道”,即指儒学而言。他认为孺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源泉,应当居于统帅地位,这表现了他的儒家本位主义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廖名缙更变本加厉,竟从维护儒学出发而排斥、诋毁新的科学知识。他在一次会讲中说:“自俗士误读进化论及《天演论》之学说,以人为脊椎之动物,上祖猿狙,吾人失其自尊自重之心,视先圣位育参赞之说为虚诞。于是秉彝攸好,含醇负性之人类,仅与儇毛蠕动者同为肉体生活之竞争,弱肉强食,浸致有今兹社会凶惨之现象。”这些话,显示了廖名缙的抱残守缺,敌视科学的顽固愚昧的态度。
(2)在对待船山学说的精华和糟粕的问题上,由于刘人熙维护传统儒学,重视封建彝伦,因而他对于船山学说中的精华部分。缺乏认识,而宣扬了其落后部分。船山在对历史上和明清之际盛行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所揭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思想;以及研究历代史事,特别是总结明朝亡国教训时所阐述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主张,是其思想中的精华。对此,刘人熙是缺乏认识的。与此相反,他对船山著作中存在较多封建糟粕的《四书训义》,却极为推崇,不仅为之刊刻、推销,而且在船山学社内向会员们先后作过十七次讲述。揆其用意,当然是希望利用船山在《四书训义》中反复论述的以辨理欲、义利和维护封建纲常为核心的学说来“正人心”。质言之,就是企图把船山这些封建说教作为抵制当时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新观念的理论武器。显然,这样做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健全和发展学社计划的周密性。刘人熙为了把船山学社办好,使之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他煞费苦心地为学社的健全和发展拟订了周密的计划,并付诸实践。
(1)争取“正学”地位。刘人熙认识到要使船山学社在湖南以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就必须使船山学说取得“正学”的地位,而要达到此目的,则非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不可。为此,刘人熙先后向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和大总统袁世凯上书或写“呈文”,说明创办船山学社有益于“世道人心”和有裨于时政的意义。袁世凯、黎元洪不仅同意创办船山学社,而且相继题写了“邹鲁津梁”、“正谊明道”的匾额,体现了船山学说的“正学”地位。
(2)建立网络型的组织。首先,刘人熙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总社,刘任总理,另设社长(廖名缙,彭政枢任此职)。接着,又在北京设立分社。北京分社于 1916年4月筹备就绪,主持人为东大陆通讯社社长张秋白,总编辑金葆光等四人,并从五月一日起在《大陆民报》开辟《船山学库》专栏。刘人熙还想在武汉设立分社,但因有在武汉设船山大学之议,故迟迟未
定。
(3)筹办船山学校。刘人熙为了培养人才,发扬船山学术思想,早就决定于船山学社中附设学校,经过一番筹划,遂于1916年创办船山学校,第二年学生多达三百人。1919年冬还选派六人赴法、英、比等国留学。
(4)开辟经常性的经费来源。刘人熙考虑到经费的充裕与否关系到船山学社的能否长久维持,因此,他非常注意开辟经费的来源。除请求政府拨款外,一方面向各界募捐(这是较大的收入),另一方面规定社员每年须缴纳二元会费。
(四)业务活动的多样性。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是一个兼有研究学术、举办教育、发行杂志、出版书籍等多门类的文化教育团体。而对会讲尤为重视,规定“每七日休沐,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这个制度到1917年10月以前,一直是坚持得好的,这从刘人熙在这年9月29日的演讲中所说的“湘中本社,每值七日休沐,会讲依然”等语可以看出。通过会讲,不仅宣扬了船山的学术思想,而且还联系当时国内外发生的某些有损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如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活动),加以揭露和谴责。由于会讲内容具有这样的现实性和进步性,所以听讲的人不断增多,由开始的“人数不甚众”,发展到百十人、几百人,最后不得不把会场搬进可容千人的大礼堂。
刘人熙筹备船山学社,历尽艰辛,终底于成。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他自己世界观的制约,他不仅没有对船山的学术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价,相反地,还把船山思想中的某些糟粕当作精华向社会传播,在当时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刘人熙搜集和刊刻船山著作,出版《船山学报》,定期向各界人士讲述船山的学说,这就空前地扩大了船山的影响,使船山学说引起国内学术界以至国外某些学者的注意,为以后科学地研究船山思想并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科——“船山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对于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的历史贡献是应当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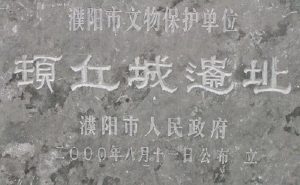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