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僻于孔子,盛于两汉,西汉中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由是大振。元、成以降进入其鼎盛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至辅相。自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需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经学的兴盛不仅对汉代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汉代的文化不能不对经学作一番探索,笔者粗撰此文旨在通过对汉代经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从一个侧面而揭示汉代文化的发展,错陋之处,敬请诸位专家教正。
(一)西汉武帝以前的经学
经学从严格意义上讲乃是指对儒家经典研究、诠释、传授的学问。“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传》曰: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从问《尚书》一篇”。经学之名虽见于汉,然经学开僻则于孔子之时,司马迁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孔子没后,孔子门人继续传播经学。据《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等。颜氏传《诗》,孟氏传《书》,漆雕氏传《礼》,仲良氏传《乐》,乐正氏传《春秋》,公孙氏传《易》。子夏尤通群经,序《诗》传《易》授《春秋》,作《丧服》。孔子既没,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弟子最盛。《后汉书•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至战国时期,经学传授形成两派,一是荀子、一是孟子,孟子是受业子思的门人传曾子之学,其从五经皆通,尤长《诗》《书》;荀子传子夏之学,善为《诗》、《礼》、《易》、《春秋》。《六经》历战国之乱而不绝于后世,荀子大有功劳。秦时,始皇焚书坑儒,经学惨遭灭顶之灾。《五经》经秦之一炬,除壁藏山匿之书未烧外,其它的所存无几。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西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天下初定,(齐)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后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文景时期,黄老思想更加盛行,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他躬身俭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景帝一遵先帝之业。“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大大抑制了经学的传播和发展。惠帝时虽下令除“挟书之律”,然《五经》传播仍不广泛。《汉书•儒林传》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五经》中除《诗》三家、《春秋》二家外,《易》、《礼》、《书》均只一家。且大都出自齐鲁之地。特别是《书》经,几乎濒临失传的地步。史载“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就《尚书》本身而言,亦是竹残简脱,多有失损。《汉书•儒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文景之世。虽已设《诗》、《春秋》博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请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在黄老思想盛行时期,尽管许多儒生以各种方式劝谏皇帝兴复经学,但都未能凑效。文帝时,贾谊曾多次上书,推崇儒家思想,他在《过秦论》中说:“(秦)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遭到周勃、灌婴、冯敬之属的反对,他们诋毁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后将贾谊排挤出朝廷。徙为长沙太傅,最后谊忧愤病死,景帝时《诗》博士辕固生在窦太后面前贬低黄老之书,将窦太后惹怒,使其赤手入圈击彘,后幸亏景帝搭救,方才幸免一死。武帝即位初,王臧,赵绾、窦缨、田蚡议立明堂,后为窦太后所知,王、赵下狱自杀;窦、田免官去职。
由上可见,经学自孔子开辟以后,虽曾称为“显学”,但由于历经战国之乱、秦火之焚,汉初又遭黄老思想盛行的抑制,所以至西汉中期一直未能得到繁荣发展。
(二)儒术独尊与经学的兴盛
武帝即位初,社会形势较汉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开始出现繁荣景象。《汉书•食货志》描述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禀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但与此同时,无为而治所造成的弊病亦愈来愈严重。在政治上,吴楚七国之乱平息之后,诸侯王势力虽被削弱,但并没有彻底铲除。他们仍暗地策划,企图推翻中央政权,“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袭爵为侯的功臣子孙居高位,依仗先辈的功劳骄奢淫逸,为非作歹,多陷法禁。在经济上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地主豪强“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他们“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以追蹵民”。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日趋严重的弊政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所以武帝即位不久,便下诏征天下贤者对策,广求治国大计。于是董仲舒出焉。
董仲舒生于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是汉代著名的公羊大师。针对汉初无为而治造成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四点政治主张。
第一、更化政治。针对诸侯王无视中央政令,各行其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混乱局面,董仲舒提出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因此他主张要善治就必须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
第二、养士求贤。针对腐朽的世袭世封制度,董仲舒竭力主张“量材而受官,禄德而定位”,他建议武帝养士求贤。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大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第三、抑制权贵。董仲舒认为豪强权贵与民争利是民不乐生,刑罚滋蕃的原因。他说:“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所以他提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
第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地方游使之士奔走各地,诸侯王将他们招至门下,着书立说,结果造成“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针对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混乱,董仲舒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向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不仅适应了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迎合了武帝的要求,因此为汉武帝所采纳。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了诸侯王的势力,打击了地主豪强的嚣张气焰。经济上改革币制,实现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制度,将财权集于中央,在文化思想领域,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定儒学为一尊,从此,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新的转机,后达到了鼎盛时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代经学得了振兴。首先《五经》博士的设立,其它博士一律废黜,使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其次太学的兴办,博士弟子员的设置,为经师儒士开辟了一条晋身入仕的禄利之途;第三任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封其为侯,唤起了人们对经学的极大兴趣。武帝以后,昭帝增置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增设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及《谷梁春秋》博士,使经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元、成时期达到极盛阶段。元成以后至东汉末年,经学一直长兴不衰。
反映汉代经学兴盛的事例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处处可见,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君臣宫闱皆读儒经。西汉初期,皇帝、太子、后宫对《五经》是不感兴趣的,“文帝好刑名之学,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好黄老之术”,经学大兴后,汉廷内外,从皇帝、太子到后宫嫔妃无不诵读经书。据史载武帝好《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宣帝受《诗》,元帝十二岁通《论语》、《孝经》,哀帝诵《诗》,东汉光武帝受《尚书》、明帝通《春秋》,章帝降意儒术,受《尚书》于汝南张酺,顺帝即位,桓焉授经禁中,皇后通经的西汉有孝昭上官后、孝成赵后。东汉有明德马后,和熹邓后,顺烈梁后等。东汉明帝时,中央曾专为四姓小侯开设宫邸学,总而言之,自儒学独尊后,汉代的君臣宫闱皆读经书。
二、诏书奏议。皆引经为据。自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经学独尊,皇帝发布诏令,群臣上奏议事,莫不旁引经说,以为依据。如武帝元朔元年春,立皇后卫氏诏令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虞唐而乐殷周,据旧而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货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此诏前后六句话,其中两句引自《易》、《诗》。
三、经师人数众多,且一师兼通数经。随着经学的兴盛,经师人数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汉代仅贯通《五经》的名师就有董仲舒、刘向、褚大、王吉、龚胜、龚舍、夏侯始昌、桓谭、尹敏、贾逵、张霸、张衡、许慎、景丹、胡广、李威、王朗等三十余人。此外刘歆,何休治六经,郑玄、马融则通十经。至于一师兼通三经、四经者,更是不计其数,举不胜举,大师众至千余人。
四、经师倍受尊宠。随着经学的发展和兴盛,经师地位大大提高。儒生不论出身贵贱,只要精通一经,便可入仕做官。显著者可为“三公”。故夏侯胜曾说:“经术高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此外很多经师以经书授太子,为太傅、太子少傅,他们更是德高望重。年迈致仕皇帝经常赐钱与他们。卒后给以厚葬,并执弟子礼。
五、经学博士及博士弟子员不断增加。武帝表章六经;初置五经博士(名立五经,实则欧阳《书》、后苍《礼》、杨何《易》。《诗》《春秋》博士文景时已立。笔者注),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时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计五家十二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二百人。元帝复立京房《易》为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复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乐经》、《左氏春秋》、为博士,(后至光武帝时废)增博士员至三十人。光武中兴,置十四博士,即齐、鲁、韩《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严、颜《春秋》,施、孟、梁丘、京房《易》,太学生增至万人。
六、私学蓬勃兴起。由于经学的广泛传播,渴求读经的人日益增多,尽管太学的博士弟子员增至千人、万人,仍不能适应广大儒生读经的要求,所以私学日渐兴盛。《后汉书•儒林传》载:张兴“梁丘《易》以教授。……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着闻,弟子自远至者,着录且万人”。据初步统计,自西汉末年至东汉,私人讲学史有明载者凡一百零三人,遍及当时二十八郡。《后汉书•儒林传》曾对当时的私学评论说:“……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羸粮功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私学的开办和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汉代经学的兴盛和普及。
七、讲论经义之风大盛,汉代讲论之风尤盛。举其大者有五:(1)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之议”;(2)元帝时朱云与五鹿充宗争论《易》之同异;(3)东汉光武帝初年范升与韩歆、陈元论立《左氏春秋》;(4)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5)和帝永元十一年鲁丕与贾逵、黄香论五经同异,讲论经义的目的有三:一是统一人们的思想,二是传播经学,促进经学的发展和繁荣,三是发现人才,凡解经有独到见解者可立为博士,令其授徒传经,这样名师高徒,历经传不衰、两汉论经著名者有朱云、井丹、丁鸿、戴凭等。东汉明帝亦曾正坐自讲,解诸儒之难。“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讲论经义之风的盛行有力促进了经学的发展。
经学在汉代所以如此兴盛,原因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两条:一是《五经》本身宣扬的内容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故自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经学的发展;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二是历代的经师儒生善于以经学奉迎统治者的需要,忠实地为统治者服务。特别是今文经师尤善发挥,一经甚至说百余万言。
经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巩固了汉朝的统治,而且对汉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表现如下:
首先是儒家的经籍得到了修整和丰富,秦火之后,儒家经籍损失惨重,竹残简缺,所存无几。汉兴,惠帝除挟书律,古文经书渐出,史载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馨琴瑟之声,逐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经学振兴之后,今文经师先是以脑记口说授经,后渐着之竹帛,解说《五经》的传、记、训、故、说、解、注、章句,日益繁多,成帝时,刘向、陈农分门别类对图书进行了校整,儒家经籍亦得到整修,随着经学的兴盛;后汉经师日众,他们不仅招徒授经,而且着书立说,如洼丹作《易通论》七篇,伏恭作《齐诗解说》九篇、卫宏着《古文尚书训旨》,牟长着《尚书章句》,马融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郑玄作《古文尚书注解》、《三礼注》,许慎作《五经异义》,何休着《公羊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据《汉书•艺文志》和《续补后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的不完全统计,自武帝至汉末,解经之书计一百多种。其中《诗》二十三,《书》二十三,《礼》二十四,《易》十三、《春秋》二十七,彻底改变了武帝初年书缺简脱的凄凉景象,儒家经籍的整理和丰富充分反映了汉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其次,经学兴盛有力地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适应经学发展的需要,汉代统治者兴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在中央设有太学。太学的学生即博士弟子,东汉称太学生,其生源主要有四:一是由太常选拔入学者;二是由郡县荐举入学者;三是因文官旨令入学者;四是自费游学者,武帝初建太学,博士弟子仅五十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后汉多达三万余人。此外中央还专门为皇亲国戚开办宫邸学,东汉明帝永平九年,曾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开办“四姓小侯学”,后不久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宿,选拔高能以受经书,安帝时,邓太后也为帝弟济北王河间王子弟四十余人以及邓氏子孙三十余人开设了一所贵胄学校。在地方上,汉代设有郡国学。景武间,蜀郡郡守文翁曾在本郡修学官,招县下子弟以先学官弟子,后武帝诏令天下以蜀郡为榜样,皆立学校官,此后地方教育日臻完善,至东汉中叶,已是“四海之内,学校林立”。就连地处边地的武威、桂阳等地也普遍开办了学校。《后汉书•循吏传》载:任延:“既之武威,……造立学官,自椽〔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在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亦如雨后春笋,蓬勃兴旺,名儒门下的生徒着录者常至万人。
第三,百家罢黜,儒术独尊窒息了其它诸家思想的发展,使汉代文化出现了单一的畸形发展趋势,在汉代文化领域,根本看不到战国末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竞放的生机,看到了的只是经学大师之间的论难相门户之争,而且他们争论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繁荣经学,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特别是今文经师任意阐发经意,将法家,道家,阴阳诸家思想融入儒学的体系,解经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神奇,越来越没生气,所以东汉之后日益衰败,玄学代之而起。此其经学兴盛对汉代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三)今古文经之争与经学的中衰
汉代经书有今古文之分,经师有今古文两派。汉初传经开始是口授耳闻,后渐着于竹帛,因书写时采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故称今文经。与今文不同,后从残垣断壁中发现的经书皆以古籀文书写,故称古文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皆今文经师。所以今文经传于朝廷,古文经多传于民间。随着经学的振兴和发展,经师地位日益提高,“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禄利之途的开僻吸引了大批的古文经师及其门徒,他们企图跻身于官学的行列,与今文经并驾齐驱,可今文经师却抱残守缺,党同伐异,坚决反对古文经立官学,这样便发生了今古文经两派之间的争论,自西汉哀帝至东汉末年,今古文经之争共掀起了三次高潮,前后持续了二三百年的时间。
西汉末年,为了适应王莽篡政的需要,刘歆掀起了今古文经之争的第一次高潮,成帝河平中,刘歆与其父刘向受诏校正秘书,后发现《春秋左氏传》大好之。且以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而《公羊》《谷梁》皆在七十子之后,故建议哀帝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为官学,哀帝遂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诸博士不肯置对,于是歆便移书太常博士,让之曰“缀学之士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群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疾,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他在书中一方面极力称赞孝宣帝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为博士的举动,另一方面攻诋今文经师“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其言甚切。对于刘歆的指责,今文经师纷纷表示不满,“诸儒皆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首先发难,他以刘歆移书深自罪责,要求辞官回家。大司空师丹则指斥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就连哀帝此时亦责备刘歆说:“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刘歆恐遭杀身之祸,便主动提出离开朝廷,到河内去做太守,今古文之争的第一次高潮就这样以刘歆的失败告终。后平帝即位王莽持政,刘歆被擢为国师,《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一度被立为官学,但不久绿林兵起,古文经不废而废。
今古文经之争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博士。光武帝不置可否,便诏在朝公卿大夫、博士会于云台论议此事,并指令范升首先发言。范升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针对范升的发言,韩歆及太中大夫许叔等进行了驳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直至日中乃罢。此后,范升又辑录《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以及《史记》违经、错引孔子之言一并上奏光武帝,光武帝再次将范升上奏交诸博士讨论。郎宫陈元诣阙上书说:“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他指责今文经师传经是“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授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并对范升所奏。《左氏》不可立所辑录的四十五事予以驳斥。他最后表示“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经过双方反复十余次争辩,最后光武帝决定将《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并以司隶从事李封为《春秋左氏》博士。《左氏》既立,今文经师即“论议欢◇,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后适逢李封病死,《左氏》遂废。今古文经之争的第二次高潮方算平息。
今古文经之争的第三次高潮起于肃宗建初年间,章帝即位,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肃宗曾先后两次诏令古文经师贾逵入宫讲经,并要他着《左氏传》长于《公羊》、《谷梁》者奏与皇上。于是贾逵便遵旨上奏说:“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今《左氏》崇君父卑巨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时有今文博士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曾著《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肃宗召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会上,李育便以《公羊》难贾逵,其论“往返皆有理正”,驳得贾逵无言以对。古文终未得立,但由于章帝特好古文,于是会后便令贾逵选严、颜(今文经博士)诸生高才者二十人以教《左氏》。后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至此,今古文经开始合流,古文经遂大行于世。
今古文经合流之后,二者之间虽不曾出现大的面对面的论战,但小的波折仍有发生,东汉末年,今文经师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再次向古文经家挑战。时古文大师郑玄便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赴废疾》以难何休,何休见而叹曰:“康成(郑玄字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然而由于章帝以后,今古文经合流已成为经学发展的主流;故何郑之争没有形成高潮,只不过是余波而已。
长达二百年的今古文经之争不仅促进了汉代经学的繁荣,而且促进了汉代科学文化的发展。首先,为了辩难,今古文经师不得不博览群经,深研精探,既要贯通今文,还要研读古文,因此东汉经学大师今古皆通,有的博通十经。如马融,一生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郑玄杂搡今古文经为一体,自成一家,号为“郑学”,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其次古文经师解经寻章摘句,往重考证,有力促进了我国训诂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研究古代文字学的杰作,至今仍闪发着夺目的光辉,此外,今古文经师在论难中,旁征博引,利用天文、地理、律历等方面的知识解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古文经家张衡就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
东汉桓灵之世,经学开始衰败,桓帝后期,宦官当道,他们把持选举,依自己的爱憎征辟官吏,从而堵塞了儒生经师入仕作官的门径。当时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他们上进无门,入仕无路,便与当朝的官僚士大夫结成一体,形成一股反对宦官集团的强大势力,在反对宦官集团的过程中,司隶校尉李膺、大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表现特别出众。有一次,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畏罪躲藏到张让家中,李膺得知,立即派人到张让家将张朔搜捕,并处以死刑。于是太学诸生便称赞他们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后不久,宦官便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下令全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百人,翌年,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公元一七二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因此再次搜捕“党人”及太学生一千余人,后下诏规定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桓灵之间,党祸两见,许多开明官僚士大夫以及太学生被逮捕下狱,禁锢终身,这对朝野的儒生经师不能不是个沉重打击。所以至东汉末年便出现了“士气颓丧,儒风寂寥”的衰落景象,据史载当时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传经授徒者仅郑玄一人而已,从而经学进入中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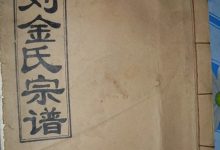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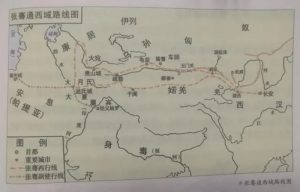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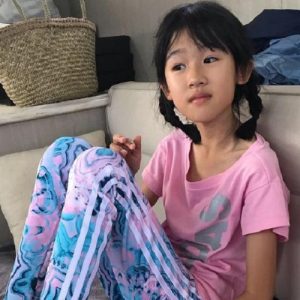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